广东连山县圣谕宣讲仪式图。
 【资料图】
【资料图】
■《法律与书商》
作者:张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法律与书商》刺破了历史的面纱,深入探究了清朝时期书商是如何推动法律的普及、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官吏阶层和普通民众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
□ 付杰
在不少人的认知中,我国封建王朝在法律上一直实行上智下愚的统治策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封建统治者意图使普通民众一直处于“法盲”的状态,自然便于统治。民间社会也有浓厚的厌讼传统,遇有争端,极少诉诸公堂,通常通过宗族、乡绅等调解来定分止争。
“举轻以明重”,清朝作为一个满族政权,又是封建专制皇权发展到巅峰的末代王朝,似乎更有动力实行传统的法律策略,便于统治庞大的汉人群体。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张婷教授的《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深入的祛魅。原来,在朴素的认知之外,历史深处还有很多有待挖掘的事实与细节。正是在这种学术挖掘活动中,历史才得以呈现出它更为生动真实的面貌。
《法律与书商》融合了清朝的法律史和出版史,作者在阅读众多文献的基础上,旁征博引,严格论证,深入考察了清朝法律图书的商业出版、统治者的法律教育与宣传策略以及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等问题,进而得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颖观点,也厘清了我们关于清朝法律教育与民众法律意识的几个迷思。
法律图书的商业出版
中国法律史课程中的清朝部分,通常只讲述《大清律例》《大清会典》、钦定各部则例等官方的成文法律,对于民间社会是否可以印刷、传播这些成文法律则付之阙如,《法律与书商》对民间如何出版法律图书进行了详尽描述。
武英殿是清朝的官方出版机构,负责刊刻朝廷出版发行的儒学、史学、医学等百家书籍,从1725年“雍正律”开始,又负责刊刻所有的钦定版清律。但武英殿是官办机构,不面向市场需求,不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图书刊刻效率低下,无法满足民间对律典的需求,这就为商业出版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有清一朝,除了雍正帝和乾隆帝时代曾颁发过对法律书籍出版的严格管控政策,其他时期对法律出版物均实行较为宽松的规制措施,清早期甚至对此不加干预,法律书籍的商业出版也就有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清早期和晚期的法律出版物要多于清中期,尤其是晚清时期,多个版本互相竞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民间出版的官方法律被简称为坊刻版。
相比于内容固定、形式单一的殿版律典,坊刻版要吸引读者购买,回应市场需求,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了重大改进,除了刊刻律典原文外,还添加了详细的律例注解、各部则例、判例、交叉索引等丰富的法律知识,并且通常有清晰明了的总索引,便于检索相关法律,因而更受社会欢迎,也更易购得,其受众群体不仅包括普通文人,还包括官员、幕友等体制或半体制人士。
可以说,坊刻版律典的商业出版与发行是一场针对官方垄断法律的去中心化运动,深刻形塑了清朝的法律教育与司法实践。
针对官员的法律培训
人们通常会认为,清朝的官员极少具备完善的法律知识,因此需要仰仗幕友协助鞫谳之事,以至于形成了“绍兴师爷”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但张婷教授通过研究发现,清朝政府十分重视朝廷官员的法律知识和实践技能,并形成了系统的法律培训制度和法律研习惯例。
清朝律典明文规定官员应掌握法律知识,“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在外各从上司官学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官罚俸一月,吏笞四十”。此外,还在诏令和规章中强调了对官员法律知识的考察,如刑部1725年宣布,所有低阶司官每年年底必须参加一次考试,背诵律典中的规定,考试成绩关系到晋升与否。
为了解决积压案件,提高司法运作效率,刑部在1860年又规定所有到部新任司官要跟现任司官学习两年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完成后方能独自办案。为了进一步规范官员法律培训制度,清朝还于1866年出台法令,推出新的法律考试形式,要求官员必须熟习法律,否则将影响晋升录用
在官员的法律培训上,清朝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审局制度。发审局负责处理京控交审案件、提省后发交案件、刑部驳回案件等,在省级司法运行系统中有重要作用,因此也就成了缺乏经验的官员观摩与研习法律的理想场所。多省都要求新任官员和候补官员须在发审局接受一年的法律培训,被评估合格后方可录用或晋升。
除了朝廷制定规章制度培养官员的法律技能外,很多官员出于仕途之需,也自觉学习法律,提升法律素养。张婷教授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官员阅读的书目,还是收藏的书籍,在四书五经、诗词文章之外,都有实用取向的法律书籍。由于坊刻版律典的兴盛,官员也易于买到此类书籍,这就为他们学习法律提供了便利。
广为流通的讼师秘本
《论语·颜渊篇》有句十分有名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追求“无讼”的伦理观念深刻影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策略,从而在民间社会中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厌讼、贱讼、耻讼情绪。但张婷教授通过研究《淡新档案》《清稗类钞》等文献,发现民众在厌讼的另一面,还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甚至利用和操纵法律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那么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了解法律知识的呢?
如上文所述,坊刻版律典虽然在市面上流通甚广,但对于底层百姓来讲,不仅价格比较昂贵,而且难以理解。他们学习法律的渠道,主要是通过低廉通俗的讼师秘本。
讼师秘本是近代中国通俗法律文学中的重要文类之一,也可以理解为通俗法律读本,主要是通过精简生动的案例、朗朗上口的歌诀、简洁明了的问答等形式传授法律知识。清朝比较流行的讼师秘本有《惊天雷》《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尽管内容简略、纸张粗糙,甚至内容也多有疏误,但由于精准拿捏了底层百姓法律需求的“痛点”,因而极受民间社会的欢迎。
不同于坊刻版律典,由于讼师秘本鼓吹诉讼,在朝廷看来无异于传播有害知识,扰乱社会秩序。尽管被严格限制在市场上流通,讼师秘本依然广泛传播。普通百姓正是通过这种渠道了解了许多有关婚姻、继承、买卖、盗窃、谋杀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他们朴素的法律意识,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法律行为。
民间社会的法律教育
清朝并非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封建统治者垄断了法律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使民众对法律处于一种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研究发现,清朝除了对官吏制定了法律培训制度,在民间社会也推行了通俗法律教育制度。当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启发民智,促进民权,而是明示法律的严酷性以威慑犯罪行为,维护统治稳定,同时发挥法律的道德教化作用,改善社会风俗习惯。
在诸多法律教育渠道中,最为重要的是圣谕宣讲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制度并非清朝首创,自宋至明都有此实践。圣谕宣讲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传统道德,还包括律典条文;宣讲形式则是借助民间乡约组织进行,到了明清时期,乡约组织的核心特征由“自愿加入、乡绅主导、地方自治组织转为强制参加、官员主导、国家支持的宣讲仪式”。
清代的圣谕宣讲更是包括大量的法律知识,这在圣谕宣讲手册中可见一斑,如最有影响力的《上谕合律乡约全书》《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均包括大量有关户律、刑律的律例原文,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通过圣谕宣讲这种大型普法形式,大量不识字、不懂法的普通百姓能够了解到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接受了最为基础的通俗法律教育。
《法律与书商》刺破了历史的面纱,深入探究了清朝时期书商是如何推动法律的普及、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官吏阶层和普通民众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这本书也打破了我们脑海中的思维定式,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律在清朝社会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统治者、民众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许书中的研究未必全然准确,但它提供了一块拼图,通过作者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求真的学术精神,拼凑出了更为完整的历史谱系,也揭开了更为真实的历史面貌。
乐活HOT
-
股票60日均线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软件上自己设置。2、60日均线是多空分界线,股价站上60日线代表
-
circle怎么读语音 circle怎么读
1、英[ˈsɜːkl]美[ˈsɜːrkl]圆;圆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驾驶电动车不遵守信号灯,被
扬子晚报网6月14日讯(通讯员张爱国记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当事
-
福建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注意!今日暴雨来袭未来三天福建以阴雨天气为主雨水上线,暂享清凉最新
-
每日热门:格力,瞎蹭流量没“销
流量时代,企业争相发力线上,变着花样引流不足为奇。即便是老牌企业如
-
余承东回应华为 5G 芯片恢复供
爱范儿早报导读披头士最后一曲,AI协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创新,着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办公场景中的扫描、传输、会议等工具,还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术体系化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近日印发《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
-
快报:【赛后】全员战至终章!热
本场赛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记者向巴特勒提问:在控
-
战舰蹈浪 列阵大洋——海军某支
作战室内,编队指挥员密切关注战场态势,指挥各舰迅速组成对空防御队
-
商务标书包括哪些内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对商务标书包括哪些内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独立标?的问题都很疑
-
移动和包APP能扫微信付款,条码
华夏时报记者付乐冉学东北京报道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发现,微信支付
-
当前讯息:沪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顺数据显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获外资卖出67 14万股,占流通
-
鄂军赢得开门红,13支三人女篮青
鄂军赢得开门红,13支三人女篮青年军鏖战江城---6月13日上午,“汉水杯
-
通信工程年终工作总结 今日热搜
我从______大学光纤专业毕业后,于8月开始在县通信分公司工作。我从事
娱乐LOVE

安徽安庆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记者日前从安庆市民政局获悉,该市慈善会近日设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该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城乡社区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积极落实2022年电网防汛度汛
近日,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110千伏中泰变电站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该公司积极落实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细化应急预案,推进极端

安徽全椒县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资源助企
今年以来,全椒县不断完善拓展人力资源信息库、劳务对接信息库、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三库信息资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业缺工岗位信息1 2万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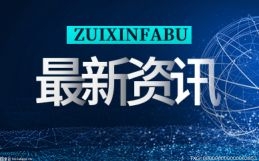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桥区柔性引进博士推进乡村振
宿州市埇桥区实施博士汇工程,柔性引进29名博士担任副乡镇长或园区副主任,他们将为加快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强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专

安徽印发出台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发《安徽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案》,明确从编制2023年预算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
近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统计数据。统计显示,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 3%,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 4个百分

安徽多种方式引导群众防范非法集资风
合肥地铁1号线、3号线上滚动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视频,淮南市发布《致老年群众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月,今

铁路部门持续加大长三角地区运力投放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为进一步适应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复工复产,铁路部门自6月10日起持续加

安徽六安持续精准施策全力促进工业发
六安市与蔚来汽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智能电动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区。该园区一期计划2023年上半年投产,建成后将具备年产30万吨铝压铸产能,

安徽淮北全力维护外卖送餐员合法权益
为切实防范化解新业态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强化外卖送餐员权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维护外卖送餐员合法权益。淮北

湖南涟源开展专项行动一对一为企业纾
位于涟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生产聚氨酯和岩棉复合板。因产品升级与产能扩充,急需新增两条生产线,

湖南蓝山县进村入户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这栋房屋墙体有开裂痕迹,要维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蓝山县塔峰镇果木村,党员干部上门开展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连日来

一季度湖南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业通信业节能监察中心发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耗统计监测报告。据该报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业的万元

济南起步区一年来累计签约优质项目11
万里黄河第一隧济南黄河济泺路隧道建成通车,占地4000余亩的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产业园加快施工……记者21日采访获悉,建设实施方案获批复一

山东发布通知启动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开展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此次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