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似乎在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真相是通过叙述与审美而呈现的一种正义。诗性正义不仅关乎审美,也关乎最本质的正义书写
□ 崔蕴华
如何阅读小说?意大利学者艾柯曾谈到自己的阅读法则:“阅读小说的基本法则是读者心照不宣地接受一个虚构约定,即柯勒律治所谓的悬置怀疑。我们接受现实世界的方式和接受虚构世界的方式并无二致。其中分野在于信任的程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艾柯不仅是美学家、符号学者,他还以写作长篇小说的方式和读者达成了虚拟契约。他的小说擅于对欧洲历史尤其是中世纪历史的审美叙述。从《玫瑰的名字》伊始,宗教派别、文献传奇、神秘符号等常常贯穿于其长篇小说中,构筑了独特的“羊皮纸小说”。此处之羊皮纸不仅是物质材质或故事背景,更是对历史的审美认知与诗性探寻,历史与虚构在小说中完美互渗、相互延展。
换言之,其小说不再简单以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或简单将历史作为背景框架进行填充。而是将历史故事化与故事历史化并置,形成大历史的严谨与审美时空的自由的独特结合。
长篇小说《波多里诺》延续了他对欧洲历史的多维书写。该小说以主人公波多里诺为义父腓特烈皇帝的大业而虚构了远东祭祀王约翰的信件和故事。从羊皮纸材质制作到故事的地域性传播,几经延展竟然成为无数人的“共识”与“信仰”。以“诗”的方式完成“史”的叙述,诗性内涵即为历史深度。
小说开篇有这么一段话:“只要有事情的片段和残迹,我就可以为你编串成带有神意的故事。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故事就这样以独特的方式和历史、意义等相关。
全书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身边的近臣也是他的义子——波多里诺为中心人物,以年迈的波氏回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经历为主,勾连出十二世纪欧洲的广阔时空。洋洋洒洒百万字的传奇回忆,对于听者、一位历史学家尼基塔斯来说兴趣盎然,他多次要求讲述者波多里诺快点讲、继续讲。
但是在小说的结尾,这些讲述却被认为是骗子的无稽之谈而无法写入史书。他被长者告之“你必须描述的是罗马帝国的真实历史,而不是诞生在远方沼泽地的关于蛮族和蛮人的轶事”。
此处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悖论,开篇信誓旦旦将故事赋予意义,结尾则以故事虚无而舍弃之。但是,真的可以舍弃吗?传奇故事似乎已经在一次次的“欺骗”和“虚幻”的话语中深植其中。这便是艾柯小说叙述的魔力与张力。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之死是小说后半部分的“悬疑”担当和叙述主脉之一。历史上,腓特烈确实于东征途中死于河水之中。这位功绩卓著、性格突出的红胡子皇帝从此消逝于历史。艾柯充分利用小说家的想象为这段历史填充了审美的意味。
以案件悬疑的方式带动历史细节,乃是作者擅长的叙述手法。腓特烈辗转于各国、周旋于各个教派,长期的征伐中不慎死于东征途中的密室。波多里诺等近臣因担心自己被诬告而合谋将“尸体”抛于河中,腓特烈大帝为何会死于密室?众人没人找到线索,于是此线索暂被搁置。十几年后,东游诸人历经险阻、侥幸逃脱魔境抵达伊斯坦布尔,在波多里诺的队友——“诗人”的布置下,通过不断拷问另外3个队友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抓住最大的嫌疑人拜占庭巫师左西摩时,却发现怀疑了十几年的凶手根本不是他,很可能是几位队友的有心无心之举“合谋”将大帝杀死在密闭的房间。而拷问队友的发疯“诗人”在癫狂中说出自己当年购买了毒药并把皇帝的解毒药偷偷置换。至此,则凶手似乎水落石出。
但是,艾柯小说玄妙之处不止于此。波多里诺将这个故事或者说是案件侦破情形讲述给拜占庭帝国史官尼基塔斯,史官则派其好友、一位博学瞽者——帕夫努吉欧来旁听故事。这位“间接”的听者经过缜密推理,冷静地推断出大帝并非中毒身亡,而是因长途旅行而吸入密室气体进入昏迷,被波多里诺等人误认为死亡而扔入河中,最终窒息而亡。
追寻十几年凶手的波多里诺竟然成为最后的凶手,这让他无法忍受。这个在无数谎言和梦幻当中不断翱翔的皇帝义子终于内心崩塌,从此在石柱上隐居自省。
“皇帝之死”的真相结局颇有审美意味。如果没有故事的讲述则不会有听者推断出真相。
更耐人寻味的是,推断出真相的竟然是眼睛无法看见真相的一位瞽者!此处让读者重新思考故事与真相、眼见为实与眼无所见的微妙关系。眼无所见也没有碰触任何证据,却在故事的言辞中可以演绎出真相。
小说似乎在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真相是通过叙述与审美而呈现的一种正义。诗性正义不仅关乎审美,也关乎最本质的正义书写。
小说后半部分以瑰丽的笔触书写波多里诺十二人去远方寻找圣杯和传奇王国,所到之处充溢光怪陆离,颇似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师徒西行之八十一难。在彭靼裴金,一行人见到美女伊帕吉雅。伊氏和波氏虽以爱情之名侃侃而谈道德、纯真,实则伊氏是波氏的精神启蒙者与审美启发者。
伊帕吉雅人面羊身,纯真无邪,其静穆哲学与纯真意念与东方美学精神相契合,既有来自印度宗教的意味,也与中国禅宗的某种精神暗自相通。12位临时拼凑的假冒“贤士”在东方之旅中不断感受艰险,最终成就了自我。
乘坐神鸟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几人,在九死一生后因寻找圣杯而发生内讧。波多里诺最终发现,他们远征寻找的圣杯竟然一直在他的行李之中。
这种描写从小说技法而言通过反转和意外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不止于此。千寻万寻却近在咫尺,这种奇幻之旅的书写令人想起中国式神魔小说《西游记》。《西游记》中取经诸人抵达西方却发现取得的真经竟然是无字经,小说中也多次提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只要你见性志成,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无论是中国人西游寻找的灵山,还是欧洲人东游寻找的圣地,千难万难只是追求内心的旅程,所寻即自身。职是之故,小说对历史的叙述超越了真假之辩与具体时空,展现出审美的翱翔意趣与自我的上下探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法治文化研究所所长)
乐活HOT
-
股票60日均线在哪里看_股票60日
1、可在软件上自己设置。2、60日均线是多空分界线,股价站上60日线代表
-
circle怎么读语音 circle怎么读
1、英[ˈsɜːkl]美[ˈsɜːrkl]圆;圆形acompletelyroundflatshapeCut
-
男子驾驶电动车不遵守信号灯,被
扬子晚报网6月14日讯(通讯员张爱国记者梅建明)6月12日上午,事故当事
-
福建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注意!今日暴雨来袭未来三天福建以阴雨天气为主雨水上线,暂享清凉最新
-
每日热门:格力,瞎蹭流量没“销
流量时代,企业争相发力线上,变着花样引流不足为奇。即便是老牌企业如
-
余承东回应华为 5G 芯片恢复供
爱范儿早报导读披头士最后一曲,AI协助完成ChatGPT推送重要更新多地高
-
聚焦:ADSCOPE:融合创新,着眼
提到工具,你想到的是什么?办公场景中的扫描、传输、会议等工具,还是
-
上海:加快“元宇宙”技术体系化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近日印发《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
-
快报:【赛后】全员战至终章!热
本场赛后,巴特勒和洛瑞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记者向巴特勒提问:在控
-
战舰蹈浪 列阵大洋——海军某支
作战室内,编队指挥员密切关注战场态势,指挥各舰迅速组成对空防御队
-
商务标书包括哪些内容(五羊本田
相信大家对商务标书包括哪些内容,五羊本田哪些是独立标?的问题都很疑
-
移动和包APP能扫微信付款,条码
华夏时报记者付乐冉学东北京报道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发现,微信支付
-
当前讯息:沪深股通|浙富控股6月
同花顺数据显示,2023年6月13日,浙富控股获外资卖出67 14万股,占流通
-
鄂军赢得开门红,13支三人女篮青
鄂军赢得开门红,13支三人女篮青年军鏖战江城---6月13日上午,“汉水杯
-
通信工程年终工作总结 今日热搜
我从______大学光纤专业毕业后,于8月开始在县通信分公司工作。我从事
娱乐LOVE

安徽安庆市正式成立“老年助餐慈善基
记者日前从安庆市民政局获悉,该市慈善会近日设立老年助餐慈善基金,共同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该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城乡社区老年食堂、社

安徽淮北积极落实2022年电网防汛度汛
近日,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110千伏中泰变电站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该公司积极落实2022年防汛度汛措施,提前细化应急预案,推进极端

安徽全椒县完善拓展人力信息资源助企
今年以来,全椒县不断完善拓展人力资源信息库、劳务对接信息库、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三库信息资源,已摸排400多家次企业缺工岗位信息1 2万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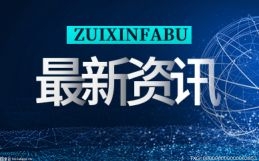
宿州市埇桥区柔性引进博士推进乡村振
宿州市埇桥区实施博士汇工程,柔性引进29名博士担任副乡镇长或园区副主任,他们将为加快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强化智力支持。目前,博士专

安徽印发出台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省政府印发《安徽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方案》,明确从编制2023年预算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

5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
近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了我省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统计数据。统计显示,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 3%,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 4个百分

安徽多种方式引导群众防范非法集资风
合肥地铁1号线、3号线上滚动播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视频,淮南市发布《致老年群众的一封信》……6月份是一年一度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月,今

铁路部门持续加大长三角地区运力投放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为进一步适应旅客出行需要,助力复工复产,铁路部门自6月10日起持续加

安徽六安持续精准施策全力促进工业发
六安市与蔚来汽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智能电动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区。该园区一期计划2023年上半年投产,建成后将具备年产30万吨铝压铸产能,

安徽淮北全力维护外卖送餐员合法权益
为切实防范化解新业态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强化外卖送餐员权益保障工作,淮北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维护外卖送餐员合法权益。淮北

湖南涟源开展专项行动一对一为企业纾
位于涟源市的湖南三合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生产聚氨酯和岩棉复合板。因产品升级与产能扩充,急需新增两条生产线,

湖南蓝山县进村入户排查整治自建房安
老叔,这栋房屋墙体有开裂痕迹,要维修加固,安全重要!5月20日,蓝山县塔峰镇果木村,党员干部上门开展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连日来

一季度湖南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近日,湖南省工业通信业节能监察中心发布一季度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耗统计监测报告。据该报告,一季度全省146家主要高耗能企业的万元

济南起步区一年来累计签约优质项目11
万里黄河第一隧济南黄河济泺路隧道建成通车,占地4000余亩的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产业园加快施工……记者21日采访获悉,建设实施方案获批复一

山东发布通知启动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部署开展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此次试点














